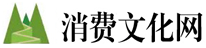杨海军:第七届中国当代实力派优秀作家
更新时间:2025-08-09 关注:5104



杨海军,男,七十年代生,甘肃定西人,县处级企干,高级政工师,党校研究生,省作协会员,出版有《春天恋歌》《问路宝天》《我的祖国河山游》等100多万字个人专著。多篇新闻与文学稿件被《人民日报》《中国交通报》《中国建材报》《甘肃日报》等采用。参与执笔的定西报系列评论获中国地市报人一等奖,《质量至上的惠民工程》获甘肃省新闻大赛一等奖、《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推进企业文化生活健康发展》获甘肃省企业党建二等奖、《怀念弟弟》获全国文华杯金奖、《最后的绝歌——爸》获“文采中国”原创文学突出贡献奖、《娘亲的味道》获“文心杯”专家评审金奖,《怀念东中》获第四届“最美中国”一等奖、《井冈红 中国红》获“觉醒时代”2025年原创文学评选奖等。

笔尖下的山河路
——我与我的文学梦想
杨海军
我的文学梦,是黄土地里长出的根脉,裹着旱塬的土腥气和土房烟火熏燎的印记。
陇中的风,四季不息,刮过定西一道道瘦骨嶙峋的山梁,深沟大壑如祖父脸上犁沟般的皱纹。儿时趴在滚烫的土炕上,目光总被爷爷那半截铅笔头牵动——他蘸着唾沫,在糊窗的旧报纸上一笔一划地记工分。“记”,是我识得的第一个字。原来最朴实的书写,竟能如房顶的椽子,硬生生撑起一个家。
儿时碎片与新闻起步
识了字,我便像旱地里盼雨的蔫苗,着了魔般搜寻所有带字的纸片:包盐疙瘩的旧报、糊墙的作业本、包红糖的糙纸壳……冬夜漫长,西北风在窗缝尖啸,我裹紧露棉的破袄,借着灶膛将熄的微光,冻红的手指在炕沿浮土里“写”下白日看来的大字:“社会主义建设”、“农业学大寨”。这些斗大的字,硬生生从冻僵的指缝钻进冷硬的童年,在穷得叮当响的日子里,孵出了一星暖光——文字真能凿透土房的沉沉黑暗,把山外的新风,一丝丝带进这闭塞的山窝。
文学的火种,在北川小学三年级的作文《麻虎》被高年级朗读时悄然点燃。到了巉口中学,胆气更盛,先在班里办起《新芽报》。学校运动会期间,一篇《巉口中学举行秋季运动会》的报道在乡广播站播放,从此一发不可收拾。“本站通讯员杨海军报道”的声音,每两三天便伴着女播音员的腔调,早中晚响彻乡间,成了小学生竞相模仿的对象。后得学校支持,创办《潮声》校报。坑洼课桌当案板,蜡纸铺开,铁笔划过如春蚕食叶。油墨滚子碾过,字迹在糙纸上晕开,那冲鼻的墨香比什么都提神。头一篇通讯写老校长:寒冬腊月,他踩着结满冰溜的羊肠小道,深一脚浅一脚,挨户劝回被爹娘叫去放羊的女娃。当带着新鲜墨味的报纸在同学手中传阅时,我远远望见老校长独自站在操场白杨树下,粗粝的手指一遍遍、小心翼翼地摩挲着报上关于他的几行字,镜片后的眼眶泛红。土房里那点模糊的光,骤然在心头炸开——原来文字不单是纸上的墨痕,更是渡人的船,能把泡在苦水里的日子,一桨一桨撑向光亮,并最终汇进自传体小说《三中:饥饿的乐园与青春的微光》。
后来在东方红中学,《中学生之友》广播站黄昏的喇叭声咿咿呀呀漫过空旷校园,少年清亮莽撞的嗓音念着同龄人的诗,滚烫句子在暮色里荡开。总有抱着柴禾生炉火的住校生,不觉放慢脚步,竖耳倾听。文字的电波穿透冰冷玻璃,在年轻的心坎上悄无声息架起一座座桥。那时我担任学校第四届学生会秘书长兼“校园之声”广播栏目主编,课外时间几乎全泡在审阅如山的稿件和指导播音上。五六人唯一的办公桌永远堆得满满当当。至今保存的审稿本里,每一笔修改,都浸透着对文字的敬畏,对青春的珍重。也是从那时起,一张张两元、五元的稿费单,像小小的火种,点燃了我与新闻、文学的不解之缘。
报社淬火与交通长歌
1995年,命运将我引向定西报社印刷厂。凭着一腔赤诚和对新闻事业的热爱,我一人挑起四五年繁重的校对重担,并利用这宝贵平台,开始了大量写作实践。消息如《定西县让教育坐第一把“交椅”》《定西老人扭秧歌庆国庆》《农民业余剧团唱响精神文明重头戏》,通讯如《黄土旱塬崛起一座美丽新城》《走进贾平凹》《余晖托起残缺的爱》《哥哥坐炕头》《旱塬披绿苦行人》,报告文学如《千年药乡传美名,走俏世界尽风流》《第二个春天》《广厦曲》……这些带着泥土芬芳的文字,如捡拾麦穗般,最终攒成了我的第一本书——四十多万字的《春天恋歌》,由甘肃人民出版社于2002年正式出版。
命运的浪头再次翻涌,将我卷入交通建设的洪流。在省交通厅工程处,钢笔与压路机形影不离。白天,扬尘蔽日的工地上,看桩基如钢钎一寸寸扎进山岩,手中的笔在小本上“唰唰”疾记;夜里,摊开被高原日头晒烫的图纸,在边角空白处捕捉筑路汉子的心跳。在白兰高速最险峻处,我遇见了《黑脸主任王化平》,记录下他蹲在硝烟未散的石碴堆上,于安全帽内衬专注演算的身影。在宝天高速的壮美画卷中,沉浸式体验催生出报告文学《问路宝天》。六条高速公路的宏伟气象,凝结成通讯《大通道作证》和史诗般的《大道行——甘肃省六条高速公路通车纪实》。这些源自山河脉搏的文字,陆续在《中国交通报》等报刊上找到了回响。
公文包的夹层里,还装着另一类“图纸”。在交通系统二十多年,三百多期党员教育简报从我手中淌过,六本两百多万字资料堆成小山。白兰、宝天项目创文明单位时,手中的笔成了夯实地基的夯锤,在皋兰县、麦积区厚厚的黄土里,一锤一锤夯实那看不见却顶要紧的“精神路基”。当十一家施工单位齐挂上“文明单位”红匾,铜牌反射的阳光与压路机新碾的沥青路面一样晃眼,心里也跟着亮堂。这些散落工地、道班、收费站的碎片故事,最终汇聚成另一部著作《白兰运营之声》。熬大夜赶稿时,窗外常飘来苦苣菜的清苦涩味——那是定西荒年活命的滋味。这气味令我猛醒:自己吭哧写下的,哪是什么轻飘飘的赞歌?分明是黄土地里挣命下扎的根须,是压路机碾过冻土时那憋在胸腔的闷哼!书出版那日,老家支书托人捎来一大包晒干的紫苜蓿花,信纸爬着歪扭的字:“认不全字哩,可闻着纸上的土腥气了,好!真格好!”
如今书架上,《春天恋歌》紧挨《大道行》,旁立《我的祖国河山游》《问路宝天》《白兰运营之声》等。烫金书脊与一摞摞《建设中的白兰高速》、《决战宝天》工程资料排列如路边的沉默里程桩。柜子深处,省交通厅“优秀信息员”红本、公航旅集团“优秀党务工作者”奖章静静躺着,像大路完工后埋进路基的界石——它们与筑路人安全帽里洗不掉的粉笔印一样,都是山河蜕变的密码,外人难懂,我心如明镜。
黄土印记与安全故事
2002年从报社调入交通系统,新公文包总不经意蹭到筑路工沾满泥灰、磨得发白的帆布裤腿。在白兰、宝天项目办间奔走,公文包里雷打不动塞着三样:印着“安全生产”的硬壳笔记本、边角磨毛的塑料皮党员手册、半块干得能砸核桃的馍——工地蹲点熬夜的救命粮。
一次钻入宝天高速石门滩隧道,正遇塌方抢险。安全帽沉甸甸压着眼皮,空气里满是粉尘与汗馊味。撤到洞口喘气,见一老工人借应急灯昏黄的光,蹲在大石上,拿短铅笔头在皱巴巴烟盒纸背面费力写着。“给孙子回信哩,”他咧嘴一笑,黄牙缝沾着泥浆,“娃问,爷爷,你修的那路,通到天边边上了不?”那歪扭用力的字迹猛地戳中我,土房里爷爷趴旧报纸上记工分的模样霎时浮现。原来路碑冰冷的里程数字,都是这些普通人用滚烫日子一笔一画写成的诗行!
2009年任宝天项目安全科科长,我琢磨出“安全故事会”的土法子。岗前培训不讲干巴道理,专讲真人真事:钢筋工老马的安全帽如何替他扛下落石;爆破员小陈的耳塞怎样在震天响里保住听力。一回讲到半截,开挖掘机的张师傅突然举起沾满油污的大手瓮声喊:“杨科!下回…下回能讲讲我么?我婆娘总嫌我回家倒头就睡,呼噜山响…”全场哄堂大笑。这片哄笑声里,纸上冰冷的安全条例仿佛被烟火气哈了一下,骤然有了活人的温度。后来,这些带着机油、汗味和笑声的故事收进《决战宝天》第一、二、三册,书页边还留着工友们黑乎乎的汗指印。
山沟记忆与扶贫财富
2013年至2017年,我扎进永靖县杨塔村扶贫五年。记忆的根,深扎在这片望不到边的贫瘠黄土地里。扛着省公航旅集团沉甸甸的期望,作为帮扶队长,一脚踩进村口的浮土,心便沉了下去:181户乡亲,95%在贫困线下挣扎,人均年收入仅1926元。山高路陡,地薄如纸。他们眼中的灰暗与那丝不敢言的期盼,像巨石压在我心口。我知道:这次,是要用指甲在这穷山沟里抠出一条活路!
破路!烂泥路捆住了乡亲手脚。集团下了大决心!领导们深一脚浅一脚钻山沟,坐土炕问冷暖。终于,5000万元的向韭公路如银带直通炳灵寺!紧接着,600万砸向山顶胜利村的游步道与停车场。我们跑项目、磨嘴皮,蚂蚁搬家般啃下10.4公里的“旅游致富路”!新路基延伸,乡亲的眼神第一次有了亮光。当最后一段沥青铺就,一位白发老汉蹲下,粗糙的手一遍遍抚摸温乎的路面,嘴唇哆嗦:“通了…真通了…山外的风,吹进来了!”黄土变作柏油,路通了,人心也活了。
点灯!守着薄地,缺技术更缺胆气。春寒料峭,农大教授地头开课:黑果枸杞、油用牡丹、枣树嫁接…乡亲们围听,眼神比娃娃上课还专注。试验田里,嫩苗怯生生顶破干硬黄土壳子——那抹绿,悄悄拱开了心头的冻土。特困户杨金莲大姐摸着送到家门口的千斤脱毒洋芋种哽咽:“这籽种…金贵!娃娃书本费,有盼头了!”数月后,她脸上笑容如山丹丹花绽放。暖棚建起,花椒飘香,洋芋蛋成了“金蛋蛋”!每一次地头开课,每一本沾泥的技术册子,都在为山沟积攒底气。
暖心!咬牙挤出130万,建起崭新的村委会、广场、卫生室。马大爷站在卫生室门口眼圈泛红:“这下好了,再不用遭罪喽!”暮色中,一盏盏太阳能路灯亮起,柔光洒满小路,也如温热泉水流进心坎。那光,照亮夜路,更照亮人心里的盼头。整街道、引净水、配设备、送温暖…点点滴滴,只为日子更舒坦、更有奔头!
五年深扎,泥土也滋养了我的笔。这份沉甸甸的成果,不仅让杨塔、胜利两村甩掉穷帽,更化作了几万字的民情日记。那些摸路的手、含泪的眼、破土的绿、点亮的灯,黄土下的坚韧与迸发的渴望,都成了最鲜活的素材。我们的故事,被省委宣传部拍成微电影《连心路》,登上电视,写入报纸。这山沟里的巨变,这土地上蓬勃的生命力,正是我文学梦想最深沉、最滚烫的源泉。扶贫的财富,不仅是修通的路、鼓起的腰包,更是刻进骨子里的山河记忆与人间烟火,它将成为我笔尖永不枯竭的力量。
墨痕灯火与红色金奖
在巡察办任副主任那些年,办公桌案头永远堆着两座“山”:左是硬邦邦的工程项目审计报告,满是数字条款;右是软乎乎沾泥带土的散文手稿。一回赶写紧急巡察汇报材料,熬至后半夜头疼欲裂。撑不住时,顺手翻开写到一半的《娘亲的味道》草稿。笔尖描到母亲佝偻着背,在老家土灶台前守着咕嘟冒热气的罐罐茶熬煮的背影,眼眶毫无防备地一酸。抬头揉揉发胀的眼,再看那堆枯燥冰冷的财务数据,奇了,竟从密密麻麻的数字缝隙里,恍惚瞧见挖掘机师傅老刘皱巴巴的医保缴费单——他女儿白血病欠下的债,原来藏在某条违规列支的项目中!后来,那篇带烟火气与人情味的民生监督建议被表扬。那一刻豁然开朗:原来冷硬的公文与温情的散文,恰如一枚硬币的两面,刻着的都是同一物——生活的纹路,百姓的冷暖。
这些年,红彤彤的获奖证书攒了不少。可最让我心头温热的,是那本不起眼的旧相册。首页贴着2009年交通厅“宝天高速公路建设先进个人”集体合影,背景是刚贯通、散发水泥味的牛背梁隧道,每人脸上汗水与自豪交织。随手翻过几页,“啪嗒”,掉出一张泛黄发脆的糙纸片——九岁那年,村头代销店软磨硬泡要来的红糖包装纸!纸背面,铅笔头歪歪扭扭写着:“我要当修路的笔”。捏着这小纸片,再看书架上印着自己名字、写满筑路故事的书,鼻尖发酸。原来真用这支笔“修”了千山万水,才懂得当年那冻出鼻涕的娃娃,凭何直觉写下那句话:在陇中这干渴旱塬上,文字与钢筋水泥一样,都是顶天立地、撑起人间山河的硬骨头、铁脊梁!
书桌玻璃板下,压着两样“镇纸”之宝:左角是老家带来的父亲当年记工分的旧报纸残片,纸黄字糊;右角是纳木错湖边老阿妈送的玛尼石拓印,经文纹路深深浅浅。每当写稿卡壳,思路如入死胡同,手指总忍不住摩挲玻璃板下这两道迥异的纹理——一道是黄土地千百年风刀霜剑刻下的粗粝掌纹;一道是雪山圣湖边经轮亿万转留下的绵长转痕。指尖微凉的触感如无声提醒:所有打动人心的书写,说到底,不过以点点墨痕,笨拙拓印脚下大地的年轮,拓印那些曾在此哭过、笑过、挣扎过、期盼过的魂灵。
这支笔也记录过冷暖人间。新闻报道如《省委书记为宝天高速公路建设者“请假”》(路桥杯好新闻三等奖)、《质量至上的惠民工程》(全省新闻大赛一等奖)、《甘肃远大路业集团“八个一”系列活动迎接建党90周年》(全省公路系统“公路杯”好新闻三等奖),调研文章如《创新机制 强化监督 切实加强远大路业集团项目建设廉政工作》(全省公路政研会优秀论文二等奖)、《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推进企业文化生活健康发展》(全省企业党建二等奖)……最让我心头沉甸的,是写亲情的文字。《怀念弟弟》是手足离别的剜心之痛,《最后的绝歌——爸》是父亲猝逝后无处诉说的思念,《娘亲的味道》是母亲留在人间烟火里的永恒印记——这些蘸泪写就的文章,竟也意外摘得全国文华杯金奖、“文采中国”原创文学突出贡献奖和“文心杯”专家评审金奖。那篇《官员 作家 孝子——陈新民的多维人生》,连老省委组织部长也赞真实感人,网上近万人阅读点赞。这些奖如路边的碑,默默标记笔尖走过的悲欢长路。
后记:未完工的路
有次驱车白兰高速,特意在当年“黑脸主任”王化平遇险的悬崖边停下。夕阳给冰冷的钢铁护栏镀上暖金。目光扫过路边敦实的水泥墩,忽见其上歪歪扭扭刻着几行小字:“王师配方 顶用”。字迹下方,一朵晒蔫的蒲公英静静压着——定是哪位路过的筑路人留下的念想。心念一动,掏出笔记本欲记此景,山风却抢先一步,“呼”地将那蒲公英吹散。带绒毛的种子纷飞如雪,飘飘摇摇,越过深谷上静卧的吊索桥,投向远方层叠的群山深处。
途经风景如画的宝天高速,壮丽山河的画卷再次铺展,沉浸其中,催生报告文学《问路宝天》的灵感。返程寻访旧踪,在当年的巉口中学,新修的塑胶跑道旁,校史栏里竟还贴着那张黑白照片——我们正伏在课桌上刻印《潮声报》蜡纸。几个穿校服的学生扒着橱窗嬉笑:“老师,这油印机,岁数怕比我阿爷还大哩?”
恰如四十多年前,土房油灯下,那个在糊窗旧报纸上描摹“社会主义建设”的冻手娃娃,何曾想到,他手中那截短短的铅笔头,终将丈量千里山河,写下百万高速长卷。此刻,轻轻合上这本浸透黄土与沥青气息的《山河路》书稿,耳畔仿佛又响起悠长的汽笛——那是文字铺就的轨道上,又一列满载人间烟火与春天故事的列车,正轰隆作响,驶向望不尽的远方。而风中的蒲公英种子,正携着最初刻在糖纸上的誓言,飞向下一片待拓印的土地。
最后的绝唱——《爸》
文/杨海军

父亲走的时候,正是疫情最猖獗的时节。街坊们说,老爷子一辈子是个热闹人,热心人,怕寂寞,爱朋友,跟着大伙赶着潮流就一块儿走了。这话有点幽默也有点安慰我们的意思,但话说得轻巧听得且很沉重,老爷子的走我们一点思想准备也没有,留给我们的失重感和撕心裂肺的疼却是如此的揪心和刻骨铭心。死亡来得太急,连告别的机会都没给,只留下电视机里那首跑调的《爸》,成了最后的绝响。
我也是疫情影响的受害者,三年疫情双亲先后撒手人寰,兰州至定西高铁半小时开车一小时的车距却是隔世的遥远,好多本该是温暖的守护和陪伴且成为终身的遗憾。知道老爷子已经“阳”了,一方面受制于严格的疫情政策,一方面觉得老爷子吉人自有天相会扛过去,所以犹豫中没有及时赶过来见父亲最后一面,陪父亲最后一程,除了遗憾还是遗憾。阳
“赶着潮流一块儿走”的黑色幽默,折射出特殊时期死亡被异化为冰冷统计数字的荒诞。街坊们用轻盈话语包裹的沉重现实,让我们在沉重中更加沉重怀念,恰似“平流层抽芽的信笺”———生者试图用语言建构通往彼岸的藤蔓,但“未寄出”的遗憾始终悬浮在生与死的平流层之间。那些被疫情模糊的告别,不仅是我个人,也将成为一代人的集体创伤记忆。
一直低调的父亲,三年前突然提出给他热热闹闹过个生日。说他爱了一辈子的秦腔,结识了一辈子的秦腔人,天天公园里听秦腔唱秦腔,大家听说老爷子当年80岁,提出生日当天中午管一顿饭,免费唱半天大家热闹一下算给老爷子过个80大寿。害怕我不同意,还让两个姐姐一直做我的工作。说我干公事限制多,不要叫任何单位和相关的人,自己和家里人来就行。就他把亲房们和自己好友叫一下,花他半年的工资热闹一下。我说八十是大寿,只要疫情允许,就按父亲的意思办吧!
说来也巧,那段时间疫情防控要求不是太紧,就给父亲在家过了一个热热闹闹的生日。生活需要仪式感,八十寿宴那日,父亲穿着我们新买的藏青色的中山服,端坐在客厅中央。衣服买大了,空荡荡地挂在他佝偻的躯干上,倒像是借来的戏服。儿女十跪父母谢恩情时,我看见父亲的眼角润湿了。跪下磕头时,却看见父亲的皮鞋已经磨出了毛边。这个细节像根刺,突然扎进了我心里,原来生活中我们还是缺失了很多。按照男左女右的传统,母亲的位置一直空着,心中的那个家一直都在,只是有了缺憾!

音乐响起时,我瞥见父亲把助听器往耳朵里塞了塞——他其实已经不太听得清了。献花时,当他接过大姐大哥献的康乃馨和向日葵时,竟有些手足无措,像两手抱着什么圣物久久不肯放下。说好的大姐大哥献花,我和尕姐唱歌,但关键时候尕姐却没了声音,我只好硬着头皮放声唱付飞社的《爸》,父亲明显既惊讶又高兴。我唱得荒腔走板,像把钝锯在木头上拉扯,亲戚们憋着笑,孩子们捂耳朵,只有父亲仰着脸,浑浊的眼睛里充满着幸福的光芒,仿佛在听大明星的演唱,布满老茧的手还在膝盖上轻轻打着拍子。
唱毕,父亲很高兴,说:"唱得很好,我很爱听,也真想多活几年陪陪他们。"众人都笑,我也笑,心里却蓦地一酸。后来他逢人就说孩子们又是献花又是唱歌的,把他真的感动了。说到孩子唱的好不好是,他总是大声说好得很,大家听着好不好不重要,他听着很亲切很幸福,大家都是鼓励他多活几年,他也有信心多活几年。
父亲向来如此,从不直言批评,总是以鼓励代之。我少时写字歪斜,他说有风骨;作文不通,他说别具一格;小事做不好,他说我儿子是做大事的人;如今我五十岁的人了,他还这般待我。父亲对我的信任,像一种跨越血缘的无声契约,也像当年鲁迅将《可爱的中国》手稿转交方志敏的经典,除了信任还是信任。平时他觉得儿子做啥都是对的,有分寸的,家里大事小事都觉得我办是最信任的,就像《困在时间里的父亲》中阿兹海默症患者故意将银行卡密码报错一位,等待儿子在纠正过程中证明自身可靠性。
后来疫情严重,我去临夏出差,被封了一个多月,中间急急忙忙看了一次父亲,回兰州又封闭了两个多月。疫情继续蔓延,前天尕姐打来电话说她和父亲都阳了,第二天媳妇自测也阳了。我说都这样了我赶下来给父亲做饭吧,电话那头,父亲的声音沙哑却坚定:好着呢,再过几天就元旦了再和媳妇一起来吧。我说那第二天我再买些东西了下来。没想到那天夜里我却收到噩耗,父亲上厕所忽然感到不舒服,摔了一下一口气没上来就走了。
简直是五雷轰顶,我根本无法相信是真的,我连父亲最后一面没见就走了。但回家望着父亲冰冷的身体,不论我如何呼唤,父亲都没有回声了。父亲走时疫情正严重,也就走的很安静。我傻傻的呆在丧铺里,静静的守着父亲,眼泪奔涌而出,天人相隔,情何以堪!有人问我,疫情已经失控,怕不怕传染,我说父亲去世了,有比这更大的事吗?哪怕生命马上受到威胁,这点坚守又有何惧!
父亲走的太匆忙。父亲总笑着说,老二,我看你房贷啥的压力很大,但我觉得你很有能力,我工资不高就不帮了,吃干挖净,我就自己花了。我说就是你就啥都想通自己花吧,啥事我兜底着呢,不够了给我说。没想到最后父亲还是留下了几万元,说给大家留个念想。我说赶快按父亲意愿赶紧给儿孙们分了,人死不能复生,大家一定要记住父亲的好。父亲一生爱热闹,大家七七纸生期纸年纸,包括前三年的守孝大家一定到。大家也都信守承诺,每遇父亲的纸大家都必在,我知道这只是我们仅能做到的对父亲最后的回报和慰藉。
父母亲的照片一直摆在我家客厅最显眼的地方,代表着这个家他们是永远的主人和最重要的人。但走过空荡荡的客厅,仿佛父亲常坐的那把太师椅还留着父亲的轮廓,耳畔还响着那首歌的旋律。有时夜深人静,我也会突然哼起那首《爸》,妻子笑我发痴,我却觉得,或许在某个平行时空里,父亲正笑着听,依然假装那是天籁之音,而我依然假装唱的很好听!对我而言,我一直坚信父亲一定会在儿子五音不全的歌声里,能听出整个春夏秋冬的变更。
父亲去世三年了,有人问我,你跟你父亲关系不好吗,母亲当年就写了《除夕长夜想母亲》,最近又写了《娘亲的味道》,很是感人,咋不见你对父亲的怀念文章。我说父爱如山,父母是这辈子最希望你好的唯二的人,对父亲咋能不好呢,只是不愿触及伤痛。母亲走了还有父亲,父亲走了感觉天真塌了,六神无主,有些痛,是巨痛,不敢碰。
昨夜梦见父亲仍然端坐客厅中央,我站在父亲面前唱《爸》歌,这次竟没跑调。父亲拍着手笑,笑着笑着,凳子就空了。醒来时,枕巾已湿。五音不全的我当年给父亲唱《爸》歌,初衷只是哄老爷子高兴,但且唱出了父亲的辛酸苦辣,唱响了父亲的幸福时刻。正如父亲所说的,别人听得舒不舒服不重要,自己的孩子给自己唱《爸》歌就是亲切和幸福。
生日过后仅仅四个月的当天,父亲就扔下我们走了。我真相信他喜欢我为他唱《爸》歌,也一定想再听一次儿子给他唱《爸》歌。这是我为父亲唱的唯一一首歌,没想到竟然成了空前绝后的绝唱,生死离别的绝唱。我知道虽唱得不堪入耳,但父亲听懂了其中之意,这就够了。
邻居们告诉我,在父亲内心,我一直是他的骄傲。父亲也是一直最认可最信任我的人,如今这种信任与认可,早已内化成我生命的一部分。父亲给予的那些被托付的重任、那些沉默的骄傲,其实是他悄悄埋在我性格里的种子。如今当他离开,我才突然发现——原来父亲早已用几十年的时间,把自己活成了我的一部分。这正是父爱最深邃的魔法:他们终将离去,却让我们成长为能承载失去的强者!
中年人的眼泪是留在人后的,生活需要负重前行。父亲的突然去世就像失重的世界,一直是说不出的痛。父亲的离世不仅是个体的失去,更是对我们自身有限性的残酷提醒。这种觉醒虽然迟缓,却也可能成为重新审视生命优先级的契机。我忽然发现自己对人际关系有了新的包容,对生活有了更本质的理解。父亲给我的信任之力,现在正以另一种形式延续——它让我在破碎中依然能保持给予爱的能力,这本身就是对他最好的致敬!

父亲去了,世界没了,大山倒了,伤心是没办法用语言描述的。我恍然大悟,原来那场寿宴,那次歌唱,是父亲在跟我们最温柔的告别。他选择了自己最爱的方式——有秦腔,有歌声,有老友,有儿女——把最后的笑容留在了阳光下。只是我们太钝,没能听出那秦腔里的离意,歌曲里的道别!
-
·叶建华|相伴诗书追雅韵 悠然践梦逐安康2024-10-31
-
·远古的呼唤,筑梦新时代 ——辜慧龙书法作品展在广州市青年文化宫隆重开幕2024-10-31
-
·文韵三晋 薪火相传——记郦道元文学院山西创作基地授牌仪式2026-02-06
-
· 高乔明 | 一场崤函深处的千年穿越——灵宝见闻漫记2026-02-06
-
·喜报!石景山区作家协会获评5A级社会组织2026-02-04
-
·中国现代文化网(报)总编、郦道元文学院执行院长林膑等一行赴山西师家沟开展调研活动2026-02-03
-
·郦道元文学院山西创作基地授牌仪式在山西临汾举行2026-02-03
-
·东方破晓 黎明照长空——写在孟黎明先生《红色记忆》付梓前夕2026-02-03
-
·庞华明:黄土高坡的文学灯塔 ——写给我心动的挚友2026-02-03
-
·于春生|骑楼老街——光耀海口的璀璨明珠2026-02-03