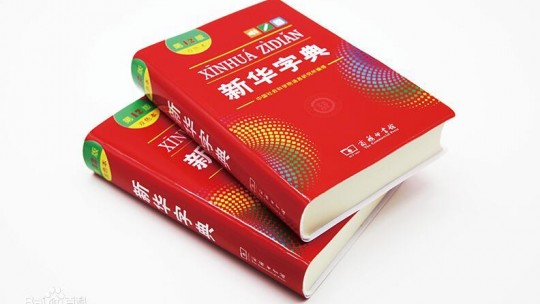文/杨景龙

诗人艾敏
多年来,诗歌阅读之于我,就像日常饮食呼吸一样,不可须臾或离。然而,在这个干冷无雪的漫长冬天,这半年紧张忙碌的倥偬日子里,我竟也久矣不复静下心来阅读诗歌了。放寒假后,心境稍觉闲暇,我才意识到这一点。不禁怆然暗惊。这时,得知诗人艾敏要出诗集的消息。于是心怀期待,打开了艾敏的诗集打印稿,开始了大半年来第一次系统集中的新诗阅读。
记得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,通过诗人地铁,我认识了艾敏,此后零星地读到地铁转来的艾敏诗作,印象颇深。那时艾敏的笔名叫郁晴,主编一份报纸的文艺副刊,也断续约我写些小诗小文。后来在市作家协会、诗词学会的活动中,经常见到艾敏,简单的问候交谈,约略知道些她的生活、工作和写诗的情况。一个需要处理繁忙事务、承担繁冗家务的女性,能够长期坚持业余读书、写作,时有佳作发表并且在全国性的诗赛中多次获奖,取得了不俗的成绩,这在书香渐缈、诗意日稀的当下,不能不格外地令人感佩。
艾敏的创作起步很早,这部诗集选入的作品,起于1980年代中期,那应该是诗人中学时代的“少作”,像《夏日》、《伞》、《花椒》、《落花生》、《那棵柳树》諸篇,但也并不显得多么稚嫩。而且,正是在这些“少作”中,初步展示了诗人的个性,预示了诗人未来的人生与创作走向。一个花季少女,最初的吟唱不是风花雪月的温馨或恼人,而是生活的严峻,现实的沉重,存在的苦难,以及对苦难的抗争。雨天的伞出现在诗歌里,多是一个带几许浪漫色彩的意象,但少年诗人笔下的“伞”,经受的是烈日烤炙,狂风撕扯,云雾威胁,暴雨击打;长条袅娜、拂水飘绵的柳树,也很宜于发抒依依柔情,但少年诗人题咏的“那棵柳树”,却是满身伤疤,枯死在断水的河床,被伐木者锯断;“夏日”被烘烤得憔悴枯黄,“花椒”遭遇灭顶之灾,“落花生”顶着凝聚的重压。但是,“伞”总在人们最需要的时刻“挺立”,“柳树”的灵魂爆出了不屈的“绿焰”,“花椒”勇敢地去赴一次“壮丽的煎熬”,“落花生”坚信“谁是强者/到秋天/果实会告诉你”。诗人早期这些比拟象征的咏物诗,托喻的是一种性格:直面现实,承受苦难,保持信念,不屈抗争。这种性格成为诗人日后创作中一以贯之的抒情基调和底色,而题咏类作品,也成为诗人日后创作中最常见的题材类别。
也许真的有所谓诗谶,也许真的是出于宿命,从吟唱现实生存的苦难开始创作的诗人,在一个没有任何异兆的秋日午后,猝然之间真个遭遇了一名年轻女性难以承受的巨大灾难。“大都好物不坚牢,彩云易散琉璃脆”,诗人原本美好的一切,都从那个脆弱的秋天的枝头倏然跌落粉碎了。从1980年代末,到1990年代中期,在长达数年的时间里,艾敏和她的诗歌都沉浸在浓郁的“悲秋”氛围里,无意间重复了一个中国诗人自古皆然的古老诗歌母题。“绵绵的秋雨”,成了“永远擦不干的泪水”,诗人与秋天“结下的是不解之恨”。虽说“世间只有情难诉”,但女诗人最是擅长抒情,《秋野独语》、《声声慢》、《让我是一株枯菊》、《祈求》、《铃兰已将你遗忘》、《中秋》、《秋天之后》等诗,把那种幽咽惨切的悲秋情绪,演绎得如怨如慕,如泣如诉。作为“悲秋”情绪的辐射和延伸,“秋天之后”依然是“孤独的春天”。春天的“花园”,在谷雨过后四月天,“依然一片荒芜”,再也“不能青青如初”。

《废墟上的梦》
然而生活不会因苦难而停止。诗人的个性也不会屈服于虐戾的命运。追求幸福是人的天性,尽管在现实中,人不免要经受痛苦的折磨。不过泪尽之后还有泪,梦碎之后还有梦。只要还有泪和梦,心中就有绚丽的未来,生活就有闪光的明天,笔下就有簇新的诗篇。从1990年代中期开始,诗人意识到既然“没有灵丹,能医爱的伤口”,那就只能“自救”。缘此,她的诗中奏出了复调,《独步》、《故人》、《故地》、《遥望》、《渴雪》和组诗《给你十四行》等,在过去与未来之间,在回忆与憧憬之间,在告别与迎迓之间,在悲怆与幸福之间,在痛苦与欢乐之间,释放出两种反向的张力。一边是难忘的刻骨铭心的记忆,一边是难抑的两美必合的欣喜。交响与变奏之中,向往新生的音调渐次嘹亮高亢。一个追求美好的人终将收获幸福。终于,在《给你十四行》里,诗人喊出了“当秋天之后/我是多么渴望”这宣告“新生”的心声。于是便有了与先生大著《邺下文人》相唱和的组诗《邺下风流》,洋溢出深层次的李清照赵明诚般的和谐欢乐。于是便有了接踵而至的《诞生》和《朝朝》,诗人全部的爱和喜悦,凝聚为“朝朝,世界将从你开始”的诗行,标志着历尽磨难之后,诗人“新生”的彻底完成。1990年代中期以后的这批复调之作,情感内涵丰沛深厚,心灵维度繁缛富赡,不仅成就了动人的诗情,更成就了美好的人格和美善的人性。
古典诗词中的女性写作,多是伤感、哀怨、缠绵的情绪宣泄或流露。由于社会文化变迁,扮演角色转换,思想资源丰富等原因,现当代新诗中的女性写作,则多表现为感性和理性的有机结合。艾敏的诗也是如此。一方面,如上所论,艾敏把情感和生命的悲喜苦乐作了充分情绪化的抒写,因其感性所以十分感人;另一方面,她的抒写又不仅仅停留在感性的层面,而是在情绪之水中析出坚实的理性结晶。《沧桑》一诗可作代表。诗中有泪水涟涟的泣诉:“一滴泪/沿着夜冰凉的面颊/凄绝地 无声息地/和着一个如水的名字/流淌 流淌/流淌了一千八百个日日夜夜”;但诗人并没有溺于咸涩的泪海不能自拔,而是毅然“将竹签 和手心上的命运/再次装入行囊,扛在肩上”,重新鼓起大无畏的生存勇气,并且辨正地看待人生的磨难,写出了“没有苦涩的人生/不能说不是人生的缺憾/没有悲剧的人生/或许才是/人生的悲剧”这样启人心智的警醒之句;并由此进至感悟命运的超越境界:“我只想如一束纯净的火焰/或者 如菩提/在盛开的莲之上/倾听红尘 静观不语”。这是一种不同于传统女性写作的现代女性写作,不仅哀婉、忧伤,而且坚韧、勇敢、超脱,诗作具有鲜明的现代意识。沧桑之后,诗人和诗歌都趋于成熟了。
王国维在《人间词话》中说:“有主观之诗人,有客观之诗人。”通观艾敏的诗作可以看到,她不仅是一个主观型的诗人,而且是一个客观型的诗人;不仅是一个情感型的诗人,而且是一个思想型的诗人;不仅是一个富有现实感的诗人,而且是一个富有历史感的诗人。这有诗集中的政治抒情长诗和咏史怀古之作为证。艾敏显然不属于那种一味沉迷个我情绪的“小女子”,她应该是入世阅世很深、现实关怀很强的现代知识女性。写抗击非典的《戴口罩的春天》,写焦裕禄精神的《与一棵树合影》,写城市农民工的《我是农民工》,写基层优秀工会主席的《写在黄河故道上的诗篇》,写现代大型企业鑫盛集团的《泰山石》,写城市新区建设的《这一片生长梦想的土地》等政治抒情长诗,均是切入现实、关注当下的重大题材之作,与时代脉搏共振,与主旋律相应和,集中体现诗人的社会责任感。这类诗多用赋体,气局开张,铺张排比,激情澎湃,是“大我”角色的放声高歌,但并不空洞说教,而往往借助典型的意象、精彩的细节、生动的修辞来表现主题。以组诗《废墟上的梦》、《易之魂》、《满江红》为代表的咏史怀古之作,则显示了女性诗人大多难得具备的厚重历史感。诗人的家乡安阳,是甲骨文的故乡,周易的发源地。“中原文化殷创始”,这里是有文字记载可考的中华文明史的开端。《易之魂》写“文王拘而演周易”,还原三千年前幽禁于羑里的那位“耄耋老人”推演周易的情景,揭示忧患中生长出的大智慧,那是我们这个历尽劫难的民族生生不息的力量的源泉。《废墟上的梦》题咏甲骨文的发现地小屯,审视殷商王朝的历史,为殷墟申遗成功而欢欣鼓舞。所谓“废墟”,就是前人留下的历史遗迹;所谓“梦”,就是今人接续前人,在辉煌灿烂的古老文明遗迹之上,创造出更为辉煌灿烂的现代文明成果;这组诗的主题是“文明的新生”,诗的标题极富象征性。多写苦难的艾敏诗歌中,隐现着一个贯穿的主题就是“涅槃与再生”,抒写个人的情感、生活如此,如《再生柳》;表现民族的历史文化亦如此,如组诗《我的黄河》和这组《废墟上的梦》。从个人的情感生活到民族的历史文化,诗人实现了诗歌题材领域和驾驭题材能力的双重跨越。这些咏史怀古之作,以其题材本身包蕴深厚的地域历史文化积淀,而昭示出一种非凡的诗歌气象。

我不知道艾敏是否读过中文系,但从其诗作中可以看出,她有着坚实的诗歌史知识积累和出色的诗歌艺术修养,对于古典诗歌和现当代新诗都能谙熟于心,信手拈来,为我所用。《我愿是一株枯菊》化用陶诗,《声声慢》仿佛后期易安词,《满江红》有岳武穆的慷慨壮烈。她的《失误》与郑愁予的《错误》,《四季青》与席慕蓉的《一棵开花的树》,《两棵树》与舒婷的《致橡树》,《给你十四行》与林子的《给他》,《情人节》与纪弦的《你的名字》,《一个农民的死》与范源的“诗小说”,《戴口罩的春天》等长诗与郭小川、贺敬之的政治抒情诗,其间均有着或隐或显的承传借鉴关系。凡此,都说明艾敏注重广泛阅读,转益多师,具有很强的对诗歌史上的名家名篇进行创造性转化的能力。
晚生的诗人是有幸的,诗歌史上辈出的名家和如林的名作,都可以成为取法的对象;晚生的诗人又是不幸的,面对名家辈出、名作如林的诗歌史,又很难再写出真正属于自己的个性和新意。在李白、杜甫写过诗之后,在艾青、北岛写过诗之后,我们还怎样写诗,这是摆在每一个晚生的诗人面前的不容回避的严峻问题。所幸“江山代有才人出”,一个真正的诗人,虽然晚生,但是经过艰辛的探索和不懈的追求,总是能够找到自己的个人意象,写出属于自己的个性和新意来。艾敏笔下的“秋天、小路、月亮、雪野、如水的名字”等意象,就是深深烙上诗人生命印痕的个人意象。她的《记忆》一诗颇富新意,不枝不蔓,简净精短的三节九行诗,尺水兴波,先把记忆喻为“一块石头”,时间的流水会把它消磨;然后“逆接”,再把记忆喻为一粒在“灵魂的伤口”里萌芽的“种子”;最后,疯长的“记忆之树结出一枚枚苦果”,任是能够消磨一切的“时间”,也“对记忆无可奈何”。可见这痛苦的记忆是多么销魂蚀骨,沥血滴髓。这首小诗,在短短的篇幅里跌宕起伏,新意频出,让人过目难忘。至于局部修辞上的出新,像《迎春花》中“忍受严寒的烧灼”一类奇特新颖、反常合道的诗句,所在多有,就不一一例举了。
艾敏无疑是一位具有足够的创作潜力的诗人。未来发展的空间很大,前路正长。如何在个人与群体之间,小我与大我之间,感性与理性之间,意识与潜意识之间,古典主义与女权主义之间,普泛写作与女性写作之间,审美价值与社会价值之间,适度协调得恰到好处,当是诗人今后诗歌创作中需要审慎应对的课题。不知艾敏以为然否?
2009年1月23日 写于扬子居