文/许江
“就脚前儿,特地撵到镇子上汇的钱,我的娃儿,我不忍心不疼呐!”
此时的张父,一把鼻子,一把泪,哽咽着攥我的手,不知恳求了多少个来回:“领导,你说咋办,我照办就是!我照办,保证不再跑风漏气了!”我心酸地应下,转身叮嘱战友小颜说:“你作好记录,把张深的身边可能要联系的人,都排查一下”。“是......”小颜迟疑了半刻,继而干脆洪亮地答道。
再看张父时,他吧嗒着旱烟袋,像个霜打的茄子,独自坐在屋前,我似乎也注意到,张父内心的不安和恐慌。我从随身的兜里摸了支香烟,陪他边抽边聊起来。
“三个娃娃,就这一个男疙瘩儿。大女娃嫁啦,二娃学着高中嘞!深娃是老疙瘩儿,惯坏了没法,孽障,我的孽啊......”张父老泪纵横地数落起过往,也颤动了我许久不动的心。前五年是老汉晚来求来的心肝,后五年是早恋少年,烧得老师家的粮仓,拎得起夜间的酒瓶,如今好吃懒做、自私骄横,人人都想衣来伸手、饭来张口,可这衣饭谁来供?
“教不住,教不住,我念着把深娃儿送去部队那大熔炉,好好磨着,砸了地,一只鸡毛都卖了,答应好好的,我求过他的啊……”老汉绷不住地哭,哭腔半开半塞,蒸得人心熟。
我没有例行公事,将他张娃儿的罪行如数列出。脑海中满是被挤压的畸形人脸,怎样的罄竹难书,能算清楚这父亲的“罪行”。是的,所谓的“父亲的罪”。入营半年不到,逃离部队三次,在部队期间,无故缺席训练、政治学习、思想情绪波动大、自闭、不合群,消极怠工。糙裂的手上,张父的旱烟一袋接着一袋,浓烈而呛鼻的烟草味身着陈旧的劣质商标,掀起了我的喷嚏,好似沉闷的谷仓透了一丁点儿缝隙。
这时,随从小颜传来侦查情报,张深刚刚挂掉和其女友的通话,并约定去临潼某中学大门口见面。“可不能再走漏风声了。”临走时,我还再三叮嘱张父。此时,饥肠辘辘和手寒脚僵已无关痛痒,我即刻甩掉手中的半截旱烟,起身告别张父。对于我来说,似乎这只是前奏,一个任务的前奏而已。但我忘不了目瞪口呆,瞠目结舌的老汉,他连声发誓:“好、好、好,我们一定配合部队”,双手作揖,不知道拜向何方。
或许,随行的“听众”和我一样,把这离开当解脱。
行动如飓风,就连我们自己也没想到,这么快就能侦查定位张深的位置。我顾不上和老汉细说,但也努力交代了注意事项,心里惦记着这上了年纪的人—他是个父亲。为防止出现意外,我急身奔了出去,随手招辆出租车。车子急速奔向目标,一路狂奔。待我到达预定地域后,我们的精兵强将们早已在各自的待机地域,专注守候,我身着军装,只得在守候区出现,便寻了个不起眼的羊肉泡馍店坐下静观。我不时地看看表,尽力忘记方才的一幕。秒针一步一步,轻松滑过。我跺一跺脚,挣开这北方的寒,饥肠辘辘,也不是这羊肉泡馍能填饱的。透着店里的香气,我的眼睛一时也没有离开目标区域,就在大家屏气凝神的时刻,时间定格在14时零5分,一个熟悉不能再熟悉的身影终于出现—传说中老父亲的心头肉。此刻,他就站在不足50米处的街上闲逛,上身穿了件不合体的、比较陈旧的黄色羽绒服,下身还是部队发的冬季作训服裤子,正脏得发亮,俨然覆盖了一抹军绿。刺猬头,黑胡茬,面显憔悴,左顾右盼地望着校园大门,等着“小相好”的“救济金”。一个10分钟悄然溜走,一个身高约一米有五的文弱女孩从校内直径向他走来。
“各小组注意!待目标交接钱物时,出击收网。”
“收到!”
“收到!”
......
对讲机内的呼吸声再次静止。张深接过300元钱团和两件灰衣服后,似乎感觉到了气氛的不对,环顾了一下四周,便丢了女友,径直跑向路边拦车。
“收网!”各组精兵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,控制了张深。此时,出逃不足半月的张深还一头雾水,惊恐和咋舌的表情。
“小子不争气,天涯海角,我们都找得到你。部队那么多战友,那么......都期望你悬崖勒马,早日归队,可你呢?”我气急败坏,却还是没能提起老汉—一位父亲的名。
“许.....长,你......怎么知道我的?......才,才半月。”我清楚时间对他的意义。
“我们在他的老家,这小子在当地对地形、地物,比我们要熟,更应该果断决定,押送返渝,及早归队,以免节外生枝。”我知道,接下来,是另一段旅程。
归队途中,他像泄了气的皮球,耷拉着脑袋,一声不吭。我询问他浪迹天涯的“自由“生活,既心疼又恼,
“宪法和兵役法是变不了框,你若能及时改正,还有机会,争取宽大处理啊!”赶去车站的路上,他始终一言不发,可我知道,即使再推心置腹,我都不能代替老汉。
时值春运,西安火车站的天色异如黑洞,攒动的人流更加重了我的隐忧。“嘿,这小子,又耍浑。”我寻着声音,神经再一次紧绷。此时的张深,是怎样的娃啊?死死抱着通道栏杆,死活不进站?还是在期待着什么转机?
为将影响降至最低,我们果断向车站公安分局求助。待说明来意后,问题如意想中顺利解决。来到车站派出所,张深变得异常乖顺,回答得全无纰漏。
“毛小子,一准儿是派出所的常客。”小颜第一次对这路人作了评论。
终于,我们登上了列车,准备轮流看守张深,生怕这小子再瞎折腾,囫囵吃了碗泡面后, 大家已经筋疲力尽,只得把张深围在中间。
不一会儿,火车急速奔驰起来了,火车开出约3小时后,张深突然提出要上厕所。春运期间,火车爆满连过道,厕所里也少不了人挤人。好不容易,他俩拥到了车厢的尽头,张深得空,一头钻进厕所,将门反锁。
近一个钟头过去了,见里面丝毫没有反应,小颜开始不停地拍打着门。情急之下,我起身挤到乘务室,向乘务员亮明身份,请求协助打开厕所门,一看究竟。乘务员得知情况,不由分说,提高特有的“嗓门”请让让,请让开通道,我和随行几人都跟着挤到厕所旁,加之不明真相的乘客围观,作为指挥员的我,也显得有些急措,但很快平静了内心。乘务员用专业的钥匙迅速打开厕所的门,映入眼帘的一切犹如老汉的烟袋般,没有一点儿亮色。厕所窗门的铁栅栏已经被破坏了两根,幸亏间距较小,人才无法脱身,此时的张深,又成了我们眼前的小丑,而不再是他父亲的儿子。我命令保卫干事小颜为其戴上特殊工具,确保类似状况再无发生。
依旧是2005年的12月某日,我的抓捕任务接近尾声。北方的冬天和南方的冬天依旧还是截然不同,我带着精兵强将、带着部队行政介绍信,次日凌晨4点抵达了古城西安站,120余时踏上了南回的列车。下车时,一股如刀刮脸的风,扑面而来,我不禁打了个哆嗦,单薄的军衣,(95式)军官单皮鞋,踩在有暗冰的地面上,一股寒气从脚到头,感觉脚上不是穿的皮鞋,而是草鞋。一步三滑的行走在站台上,走出车站,我和随从的战友面面相觑,会意地笑了,脸颊,鼻子都冻得红扑扑,嘴巴也僵硬了,只能“含糊听音”。回想追捕途中:我、张深、老汉、随行人员几乎没有休息合眼,列车呼啸着穿过山岭,我望着窗外山岭上的时厚时薄的积雪,思绪在既定抓捕方案中不断徘徊,把情况想得复杂些,把问题想得更细致些。
后来,我见到了传说中不合格的父亲,一个地道的,老实巴交的农民,一口陕西地道口音,情绪激动但有些闪烁其词。我作为橄榄色的代表,努力克制情绪,用普通话耐心地告诉其子在部队的各项劣性表现:“此次逃离部队,已经是第三次,已经触犯宪法及部队的《条令条例》。本着部队从关心战士个人成长进步,个人的前途未来以及惩前毖后,治病救人的方针,希望早日归队,及时处罚,消除不良影响。”如此动之以情,晓之以理,使其父失声痛哭起来,说担心娃子在部队吃了“苦头”,所以没有和部队领导讲真情。
他走投无路,告诉父亲,已无颜回乡面见父老乡亲、亲戚朋友,他要浪迹天涯。
老汉听了,二话没说,抖了抖烟灰,抿抿,想都不想就放进嘴里,试想,谁会怪罪一位父亲?

作者简介
许 江
中共党员
原成都军区某部副参谋长
中国现代作家协会会员
北京写作学会文化艺术促进会理事
南国作家学会理事
南国文学杂志社签约作家
南国文学重庆渝中社社长
业余爱好:创作诗歌、散文诗、摄影。
其散文、诗歌代表作品有《追捕》《盼春归.山城》《孤独的夜里,总有一盏灯》《战疫中 我若牺牲》《曙光》《静待花开》《好兄弟.归来兮》等作品,散见于人民日报人民号、中国现代文化网、腾讯新闻、上游新闻、今日头条、搜狐新闻、新浪新闻、一点资讯、南国文学,诗行天下、兰娟雅苑、山溪水、真的爱读、音悦诵等媒体平台。先后被中国现代文化报刊管理出版社、中华现代文学艺术促进会、北京写作学会、全国郦道元山水文学大赛组委会评为:第二届中国实力派优秀作家、全国第六届道德教育新闻人物、2020最美作家等荣誉称号。

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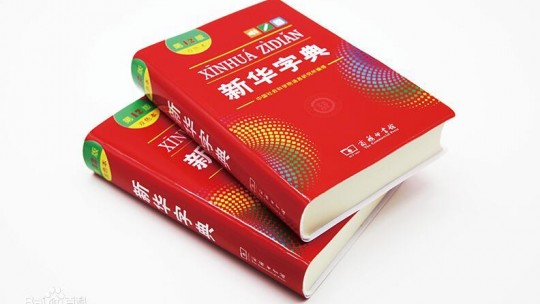



我要评论